剧照剧照影片描述的是亚美尼亚一位十八世纪游吟诗人的故事,这不是一部传记影片,而是一首关于这位诗人的精神影像的诗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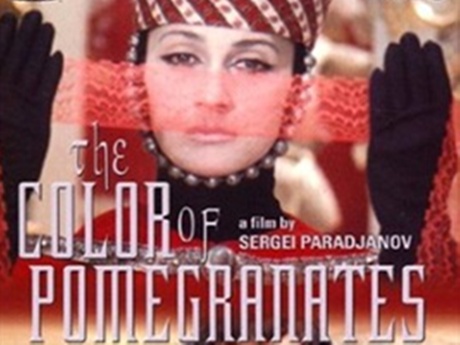 想要用文字来概括这部影片,是徒然的
想要用文字来概括这部影片,是徒然的 片中运用大量象征、隐喻手法,展现了十八世纪亚美尼亚民族风貌和这位诗人的心路历程
片中运用大量象征、隐喻手法,展现了十八世纪亚美尼亚民族风貌和这位诗人的心路历程 欣赏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次观影,更是一次朝圣,一次对诗意精神的膜拜之旅
欣赏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次观影,更是一次朝圣,一次对诗意精神的膜拜之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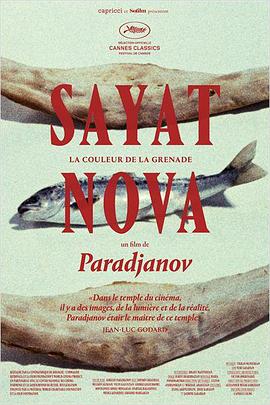 Poet as a YouthSofiko ChiaureliPoet as a childMelkon AleksanyanPoet in the cloisterVilen GalstyanPoet as an old manGiorgi GegechkoriPoet's fatherSpartak BagashviliPoet's motherMedea DjaparidzePrinceHovhannes Minasyan谢尔盖·帕拉杰诺夫Sayat Nova、谢尔盖·帕拉杰诺夫剧照剧照本片在1968年苏联当局审查的时候,被强行重新剪辑并且改名字,电影原来的名字是Sayat Nova萨雅·诺瓦,更名为The Color of Pomegranate石榴的颜色,禁止放映和发行 1969年根据该片而拍摄的记录片The Color of Armenian Soil(亚美尼亚人灵魂的颜色)同样遭到禁映 电影胶片在20年之后,Mikhail Vartanov的记录片Parajanov: The Last Spring (1992) 中重新出现,还包括有Sayat Nova的介绍和关于电影独特语言的说明 人们可以看到的DVD版本,最先最完整的发行时间是在1992年 这一版本在1969年送到苏联审查局的时候,遭到强烈反对并且重新剪辑了大部分 有一个比导演剪辑的更加完整时间更长的版本还在亚美尼亚电影档案的某个地方存放着 剧照剧照手法自由抒情,如同一首奔放而艳丽的散文诗,还有宗教仪式和宗教意念 片中充满象征和隐喻手法,结尾处的战士向诗人射箭而在墙上渗出血迹,暗喻波斯侵略者在教堂前谋杀了该诗人 整部电影没有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但色彩鲜艳,亚美尼亚的民族风貌也很浓郁 本片在苏联遭到长时间禁映,在1973年由另一位名家尤特凯维奇拿出来,重新以《石榴的颜色》为名在苏联少数艺术类影院放映 日期奖项方获奖方获奖情况2014年第67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经典修复单元《石榴的颜色》入围2022年12月《视与听》影史最伟大100部影片导演版 《石榴的颜色》入选制作公司1 Armenfilm Studios发行公司1 International Film Exchange Ltd (IFEX)[美国](1987) (USA) (subtitled)2 Artkino Pictures Inc [美国]参考资料:上映日期国家/地区上映/发行日期(细节)苏联Soviet Union1968年8月29日 (Yerevan, Armenia)瑞典Sweden1984年8月17日英国UK1999年11月26日 (director's cut)参考资料:剧照剧照在诗人的梦境里,吟游是一种最诗意的常态 而《石榴的颜色》便是这样一场关于吟游的梦境 作为谢尔盖·帕拉杰诺夫穷尽其身的诗电影杰作,本片无疑是前苏联光影圣殿中的一场绝美祭礼 在年幼懵懂的儿时梦境里,帕拉杰诺夫一次次将作为少年的自己投掷进须臾的光影洪流,那一刻,少年附首贴耳,倾听大地的诗句 时隔多年,他将诗人的时空与自己的梦境奇妙缔结,终于拍出这一部《石榴的颜色》 影片中,借助诗人之口,帕拉杰诺夫道出了艺术的真谛:一个诗人也许会死,但是他的缪斯不死 两个吟游诗人《石榴的颜色》诞生于1968年,正值举世震惊的“布拉格之春”事件 这一年,塔可夫斯基正处于拍完《安德烈·卢布廖夫》后的休整期,而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才刚刚开始他的电影生涯 对于帕拉杰诺夫而言,这是最坏的时期,也是最好的岁月 政治对于电影的管束渐趋于禁忌,而艺术家的创作使命却迸发出悲天悯人的底色 毋庸置疑,帕拉杰诺夫一反常态的独特手笔,使《石榴的颜色》在诞生之初便名声大噪,更一度被评论界誉为“前苏联冷战时期最出色的一部电影” 在帕拉杰诺夫的这部杰作中,注定被放进了两位吟游诗人 其中一位是影片的主角,十八世纪亚美尼亚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萨雅·诺瓦;而《石榴的颜色》英译版原名“Sayat Nova”便源自于此 另一位诗人则是帕拉杰诺夫自己,他的个人喜好与私我哲学,都被熔铸进这场永恒而遥远的历史长梦中 这场祭礼般的长途跋涉,固然是对萨雅·诺瓦的诗意传承,但更多的精神元气恐怕更属于帕拉杰诺夫自己 在《石榴的颜色》中,帕拉杰诺夫天才地呈现了一个制度上的现实:在这看似自由的王国里,每个人都处于他自己的位置,他们各司其职,勤勤恳恳 他们踩着各自的木梯上上下下,他们在自己的染缸旁挑出一匹匹布料,她们在各自的纺纱机旁不停地纺纱,甚至于他们胯下的马驹也有固定的路径 在帕拉杰诺夫眼中,这看似是一个时代的安稳祥和,却更是一个时代的莫大悲哀 这一刻,作为吟游诗人的少年,在半梦半醒中,也渐渐走向了陌生而遥远的自己 值得玩味的是,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面无表情,不苟言笑,无论他们的身边正经历着什么,劳作、阅读、示爱、洗礼、屠宰、战乱、祷告,甚至死亡,每个人都仿佛经历一场场仪式的历史人物,没有温度 或许,他们的体温久已被绮丽的布景所稀释,而影像的色调冷暖便是他们的温度 无独有偶,帕拉杰诺夫的这番处理无疑是世界性的手笔;而对于唯明星与表演马首是瞻的好莱坞而言,固然是不会明白其间妙处的 与帕拉杰诺夫一样,法国导演布列松也一度拒绝演员表演,在他的电影里,所有演员同样都是面无表情 但不同的是,布列松更借此倾向于电影的作者性,而帕拉杰诺夫则更倾向于对一个时代静物式的仪式性描摩 在仪式里,人物没有喜怒哀乐,他们的表情都被一种肃穆感所笼罩 而或许,正像有人揣度的,《石榴的颜色》的温度更是内性的,它不是通过人物的表情来传达,而是通过人物的内心 正如帕拉杰诺夫自身所言:我并不试图讲述一位诗人的生活,而是尽力再现一位诗人的内心世界 纵观《石榴的颜色》的段落式结构,从“诗人的童年”到“诗人的青年”,及至诗人被杀死后的“最终的葬礼”,漫漫人生之旅或许莫不如此,却似乎又各有不同 在这场独属于诗人的人生梦境中,我们仿佛也看见自己的影子,被一寸寸深烙于诗句中 亚美尼亚巫术剧照剧照帕拉杰诺夫让人着迷的地方,是他与英国导演德里克·贾曼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 贾曼惯于将炼金术投注于影像,而帕拉让诺夫则在胶片中注入了一股巫性的气息 在《石榴的颜色》中,帕拉让诺夫并没有任何直接表现巫术的段落,但不容置疑的是,他的镜头语言却是充满巫性的,无论从摄影、布景,还是演员的表演上,都像被施了巫术一般,奇妙而诡谲 与此同时,影片对于整个中世纪的长卷式描摩也充满着巫气 比如在兵戈相接的战场一幕,一群异人在偌大的空地上不间断表演,仿佛各司其职的天体永动机 再比如宗教祭祀场面中,牧师将成群的羔羊圈进教堂,让人想及牧羊人神谕,又想及卡尔维诺笔下的黑羊 或许,这些都只是我庸人自扰的蓄意揣度罢了,关于象征隐喻的外延性,优劣各见 至于对影像的肃穆姿态与游戏精神之间的拿捏,我不好说 我唯独明白,此时此刻,我仿佛成了第三个游吟诗人,在电影中寻找着自己 细细回想帕拉让诺夫的另一部杰作《被遗忘的祖先的阴影》,则似乎有着更明显的巫性气息,关于民族探索生存道路的魔幻手笔,仿佛穿行于奇幻和真实之间 犹记得文学界昔日对于“神话”本源的探寻,同样离不开“巫”字,而东西方的祖先们,又是寄寓巫性的最佳神话载体 有幸的是,借着帕拉杰诺夫的影像表达,这份独属于亚美尼亚的巫气,在日后的俄罗斯电影中亦闪耀出薪火相传的微光,比如亚历山大·罗戈日金导演拍于2002年的《布谷鸟》,就有过一幕召唤灵魂的巫术瞬间 回至《石榴的颜色》,不得不提的还有那一场诡异的洗礼 借先辈之手,帕拉杰诺夫将圣水施洗于一具“木乃伊”,一如施洗于“死亡”,而非“新生” 或许,对诗人而言,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更只是归于尘土的稀松平常 这一刻,帕拉杰诺夫对于生死的哲学念想也悄然隐现 于他而言,死亡与新生的距离,唯独只是一场洗礼罢了,就像日夜轮转的间隙,静静睡了一大觉 边陲文明遥想剧照剧照关于《石榴的颜色》的珍贵之处,自不待言 帕拉杰诺夫对于亚美尼亚远古文明的细腻展现,让我们有幸得见一个边陲国度的生死荣辱 昔日对于亚美尼亚的遥想,或许仅仅是吉光片羽,而在帕拉杰诺夫的影像中,这些琐碎的瞬间被一一串联,成为一场永恒的生命的祭礼 这一刻,电影有了生动的灵魂,即便影像中充斥着自由的禁锢和命运的籓篱,却恐怕再也没有更美的梦境了 影片中,帕拉杰诺夫全然摒弃了运动镜头,而谨以固定机位注视着一个个或动或静的瞬间 作为导演,他对于石榴与水果刀的注视有如静物写生 这一刻,石榴在白色布匹上晕染开鲜血般素艳的红色 继而是一把古旧的匕首,同样在白色布匹上晕染开鲜血般的红色 于是,石榴的颜色开始萌生出暴力与杀戮的历史象征意味 而对于游走于画面中的人物,导演的拍摄手笔同样有如静物一般 剧中人仿佛被舞台操控的人偶,面无表情,唯独专注于手头的劳作,仿佛有种古老的气息孕育其中 其中一幕荆棘密布黑色底板的画面,则让我想及塔可夫斯基《潜行者》中的荆棘头环 在表现亚美尼亚独有的祭祀、洗礼等仪式时,影像的构图则以平面式的局部全景,呈现出一种奇妙的舞台感 与其他导演不同的是,帕拉杰诺夫的舞台既没有棱角,也没有翻转,而更像是流浪艺人所建构的最原始的小舞台,一切生离死别都展现于固定的取景框中 在这个舞台上,演员只能水平进退,而不能上下坡,他们的举手投足只属于地平线 在诗人的一连串内心历程中,“诗人的童年”无疑是最绮丽多彩的,帕拉让诺夫将少年的好奇心展现得甚为迷人 无论是纺纱的母辈,染布的父辈,抑或屠宰场的鸡群,都呈现出一种漂亮的红色 在少年眼中,这些红色尚且还是纯粹的,还没有黑暗的成人世界的投影 诗人的童年,仿佛有一种奇妙的节律,先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一种永恒的轮回 浸水的书籍用石块压榨出水分,在屋顶上一排排晾晒 少年躺在阳光下,一如畅游书海的冒险家 关于压书一幕,一度令我想及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小说中的苍老的艺术家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将一捆捆旧书与艺术品打包,放入碾书机 影片最后,帕拉让诺夫抛下了一个永恒的“艺术”母题:一个诗人也许会死,但他的缪斯不死 对诗人而言,他的诗句是不朽的 正如对帕拉让诺夫而言,他的影像也是不朽的 他们的缪斯便是艺术载体在精神层面的永恒延伸
Poet as a YouthSofiko ChiaureliPoet as a childMelkon AleksanyanPoet in the cloisterVilen GalstyanPoet as an old manGiorgi GegechkoriPoet's fatherSpartak BagashviliPoet's motherMedea DjaparidzePrinceHovhannes Minasyan谢尔盖·帕拉杰诺夫Sayat Nova、谢尔盖·帕拉杰诺夫剧照剧照本片在1968年苏联当局审查的时候,被强行重新剪辑并且改名字,电影原来的名字是Sayat Nova萨雅·诺瓦,更名为The Color of Pomegranate石榴的颜色,禁止放映和发行 1969年根据该片而拍摄的记录片The Color of Armenian Soil(亚美尼亚人灵魂的颜色)同样遭到禁映 电影胶片在20年之后,Mikhail Vartanov的记录片Parajanov: The Last Spring (1992) 中重新出现,还包括有Sayat Nova的介绍和关于电影独特语言的说明 人们可以看到的DVD版本,最先最完整的发行时间是在1992年 这一版本在1969年送到苏联审查局的时候,遭到强烈反对并且重新剪辑了大部分 有一个比导演剪辑的更加完整时间更长的版本还在亚美尼亚电影档案的某个地方存放着 剧照剧照手法自由抒情,如同一首奔放而艳丽的散文诗,还有宗教仪式和宗教意念 片中充满象征和隐喻手法,结尾处的战士向诗人射箭而在墙上渗出血迹,暗喻波斯侵略者在教堂前谋杀了该诗人 整部电影没有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但色彩鲜艳,亚美尼亚的民族风貌也很浓郁 本片在苏联遭到长时间禁映,在1973年由另一位名家尤特凯维奇拿出来,重新以《石榴的颜色》为名在苏联少数艺术类影院放映 日期奖项方获奖方获奖情况2014年第67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经典修复单元《石榴的颜色》入围2022年12月《视与听》影史最伟大100部影片导演版 《石榴的颜色》入选制作公司1 Armenfilm Studios发行公司1 International Film Exchange Ltd (IFEX)[美国](1987) (USA) (subtitled)2 Artkino Pictures Inc [美国]参考资料:上映日期国家/地区上映/发行日期(细节)苏联Soviet Union1968年8月29日 (Yerevan, Armenia)瑞典Sweden1984年8月17日英国UK1999年11月26日 (director's cut)参考资料:剧照剧照在诗人的梦境里,吟游是一种最诗意的常态 而《石榴的颜色》便是这样一场关于吟游的梦境 作为谢尔盖·帕拉杰诺夫穷尽其身的诗电影杰作,本片无疑是前苏联光影圣殿中的一场绝美祭礼 在年幼懵懂的儿时梦境里,帕拉杰诺夫一次次将作为少年的自己投掷进须臾的光影洪流,那一刻,少年附首贴耳,倾听大地的诗句 时隔多年,他将诗人的时空与自己的梦境奇妙缔结,终于拍出这一部《石榴的颜色》 影片中,借助诗人之口,帕拉杰诺夫道出了艺术的真谛:一个诗人也许会死,但是他的缪斯不死 两个吟游诗人《石榴的颜色》诞生于1968年,正值举世震惊的“布拉格之春”事件 这一年,塔可夫斯基正处于拍完《安德烈·卢布廖夫》后的休整期,而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才刚刚开始他的电影生涯 对于帕拉杰诺夫而言,这是最坏的时期,也是最好的岁月 政治对于电影的管束渐趋于禁忌,而艺术家的创作使命却迸发出悲天悯人的底色 毋庸置疑,帕拉杰诺夫一反常态的独特手笔,使《石榴的颜色》在诞生之初便名声大噪,更一度被评论界誉为“前苏联冷战时期最出色的一部电影” 在帕拉杰诺夫的这部杰作中,注定被放进了两位吟游诗人 其中一位是影片的主角,十八世纪亚美尼亚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萨雅·诺瓦;而《石榴的颜色》英译版原名“Sayat Nova”便源自于此 另一位诗人则是帕拉杰诺夫自己,他的个人喜好与私我哲学,都被熔铸进这场永恒而遥远的历史长梦中 这场祭礼般的长途跋涉,固然是对萨雅·诺瓦的诗意传承,但更多的精神元气恐怕更属于帕拉杰诺夫自己 在《石榴的颜色》中,帕拉杰诺夫天才地呈现了一个制度上的现实:在这看似自由的王国里,每个人都处于他自己的位置,他们各司其职,勤勤恳恳 他们踩着各自的木梯上上下下,他们在自己的染缸旁挑出一匹匹布料,她们在各自的纺纱机旁不停地纺纱,甚至于他们胯下的马驹也有固定的路径 在帕拉杰诺夫眼中,这看似是一个时代的安稳祥和,却更是一个时代的莫大悲哀 这一刻,作为吟游诗人的少年,在半梦半醒中,也渐渐走向了陌生而遥远的自己 值得玩味的是,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面无表情,不苟言笑,无论他们的身边正经历着什么,劳作、阅读、示爱、洗礼、屠宰、战乱、祷告,甚至死亡,每个人都仿佛经历一场场仪式的历史人物,没有温度 或许,他们的体温久已被绮丽的布景所稀释,而影像的色调冷暖便是他们的温度 无独有偶,帕拉杰诺夫的这番处理无疑是世界性的手笔;而对于唯明星与表演马首是瞻的好莱坞而言,固然是不会明白其间妙处的 与帕拉杰诺夫一样,法国导演布列松也一度拒绝演员表演,在他的电影里,所有演员同样都是面无表情 但不同的是,布列松更借此倾向于电影的作者性,而帕拉杰诺夫则更倾向于对一个时代静物式的仪式性描摩 在仪式里,人物没有喜怒哀乐,他们的表情都被一种肃穆感所笼罩 而或许,正像有人揣度的,《石榴的颜色》的温度更是内性的,它不是通过人物的表情来传达,而是通过人物的内心 正如帕拉杰诺夫自身所言:我并不试图讲述一位诗人的生活,而是尽力再现一位诗人的内心世界 纵观《石榴的颜色》的段落式结构,从“诗人的童年”到“诗人的青年”,及至诗人被杀死后的“最终的葬礼”,漫漫人生之旅或许莫不如此,却似乎又各有不同 在这场独属于诗人的人生梦境中,我们仿佛也看见自己的影子,被一寸寸深烙于诗句中 亚美尼亚巫术剧照剧照帕拉杰诺夫让人着迷的地方,是他与英国导演德里克·贾曼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 贾曼惯于将炼金术投注于影像,而帕拉让诺夫则在胶片中注入了一股巫性的气息 在《石榴的颜色》中,帕拉让诺夫并没有任何直接表现巫术的段落,但不容置疑的是,他的镜头语言却是充满巫性的,无论从摄影、布景,还是演员的表演上,都像被施了巫术一般,奇妙而诡谲 与此同时,影片对于整个中世纪的长卷式描摩也充满着巫气 比如在兵戈相接的战场一幕,一群异人在偌大的空地上不间断表演,仿佛各司其职的天体永动机 再比如宗教祭祀场面中,牧师将成群的羔羊圈进教堂,让人想及牧羊人神谕,又想及卡尔维诺笔下的黑羊 或许,这些都只是我庸人自扰的蓄意揣度罢了,关于象征隐喻的外延性,优劣各见 至于对影像的肃穆姿态与游戏精神之间的拿捏,我不好说 我唯独明白,此时此刻,我仿佛成了第三个游吟诗人,在电影中寻找着自己 细细回想帕拉让诺夫的另一部杰作《被遗忘的祖先的阴影》,则似乎有着更明显的巫性气息,关于民族探索生存道路的魔幻手笔,仿佛穿行于奇幻和真实之间 犹记得文学界昔日对于“神话”本源的探寻,同样离不开“巫”字,而东西方的祖先们,又是寄寓巫性的最佳神话载体 有幸的是,借着帕拉杰诺夫的影像表达,这份独属于亚美尼亚的巫气,在日后的俄罗斯电影中亦闪耀出薪火相传的微光,比如亚历山大·罗戈日金导演拍于2002年的《布谷鸟》,就有过一幕召唤灵魂的巫术瞬间 回至《石榴的颜色》,不得不提的还有那一场诡异的洗礼 借先辈之手,帕拉杰诺夫将圣水施洗于一具“木乃伊”,一如施洗于“死亡”,而非“新生” 或许,对诗人而言,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更只是归于尘土的稀松平常 这一刻,帕拉杰诺夫对于生死的哲学念想也悄然隐现 于他而言,死亡与新生的距离,唯独只是一场洗礼罢了,就像日夜轮转的间隙,静静睡了一大觉 边陲文明遥想剧照剧照关于《石榴的颜色》的珍贵之处,自不待言 帕拉杰诺夫对于亚美尼亚远古文明的细腻展现,让我们有幸得见一个边陲国度的生死荣辱 昔日对于亚美尼亚的遥想,或许仅仅是吉光片羽,而在帕拉杰诺夫的影像中,这些琐碎的瞬间被一一串联,成为一场永恒的生命的祭礼 这一刻,电影有了生动的灵魂,即便影像中充斥着自由的禁锢和命运的籓篱,却恐怕再也没有更美的梦境了 影片中,帕拉杰诺夫全然摒弃了运动镜头,而谨以固定机位注视着一个个或动或静的瞬间 作为导演,他对于石榴与水果刀的注视有如静物写生 这一刻,石榴在白色布匹上晕染开鲜血般素艳的红色 继而是一把古旧的匕首,同样在白色布匹上晕染开鲜血般的红色 于是,石榴的颜色开始萌生出暴力与杀戮的历史象征意味 而对于游走于画面中的人物,导演的拍摄手笔同样有如静物一般 剧中人仿佛被舞台操控的人偶,面无表情,唯独专注于手头的劳作,仿佛有种古老的气息孕育其中 其中一幕荆棘密布黑色底板的画面,则让我想及塔可夫斯基《潜行者》中的荆棘头环 在表现亚美尼亚独有的祭祀、洗礼等仪式时,影像的构图则以平面式的局部全景,呈现出一种奇妙的舞台感 与其他导演不同的是,帕拉杰诺夫的舞台既没有棱角,也没有翻转,而更像是流浪艺人所建构的最原始的小舞台,一切生离死别都展现于固定的取景框中 在这个舞台上,演员只能水平进退,而不能上下坡,他们的举手投足只属于地平线 在诗人的一连串内心历程中,“诗人的童年”无疑是最绮丽多彩的,帕拉让诺夫将少年的好奇心展现得甚为迷人 无论是纺纱的母辈,染布的父辈,抑或屠宰场的鸡群,都呈现出一种漂亮的红色 在少年眼中,这些红色尚且还是纯粹的,还没有黑暗的成人世界的投影 诗人的童年,仿佛有一种奇妙的节律,先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一种永恒的轮回 浸水的书籍用石块压榨出水分,在屋顶上一排排晾晒 少年躺在阳光下,一如畅游书海的冒险家 关于压书一幕,一度令我想及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小说中的苍老的艺术家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将一捆捆旧书与艺术品打包,放入碾书机 影片最后,帕拉让诺夫抛下了一个永恒的“艺术”母题:一个诗人也许会死,但他的缪斯不死 对诗人而言,他的诗句是不朽的 正如对帕拉让诺夫而言,他的影像也是不朽的 他们的缪斯便是艺术载体在精神层面的永恒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