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古代的医学典籍中记载的许多医学知识,实际上都是在人体上观察到的自然事件 但医学如果只限于记录自然遇到的事件,就只能描述现象,而不能成为有意识地探索未知领域的真正的科学
但医学如果只限于记录自然遇到的事件,就只能描述现象,而不能成为有意识地探索未知领域的真正的科学 由于对疾病的本质缺乏可靠的认识,这种治疗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由于对疾病的本质缺乏可靠的认识,这种治疗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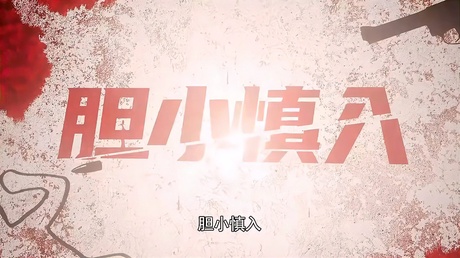 虽然盲目的摸索也曾取得一些十分有用的经验,如罂粟的止痛、金鸡纳霜(奎宁)的制疟等
虽然盲目的摸索也曾取得一些十分有用的经验,如罂粟的止痛、金鸡纳霜(奎宁)的制疟等 但是靠“拾取”这种偶然发现来积累经验,医学的进步就会是十分缓慢的
但是靠“拾取”这种偶然发现来积累经验,医学的进步就会是十分缓慢的 只有当医学引进科学实验的方法,有意识地向自然“索取”知识时,医学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只有当医学引进科学实验的方法,有意识地向自然“索取”知识时,医学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医学中的科学实验最初是在动物中进行的,如英国的医生W
医学中的科学实验最初是在动物中进行的,如英国的医生W 哈维(1578~1657)在狗身上发现了“动物的心血运动”──血液循环
哈维(1578~1657)在狗身上发现了“动物的心血运动”──血液循环 以后又经过许多优秀医学家的努力,医学中的科学实验才逐渐发达起来
以后又经过许多优秀医学家的努力,医学中的科学实验才逐渐发达起来 1865年法国医学家C
1865年法国医学家C 贝尔纳(1813~1878)发表《实验医学导论》,论证了在医学中采用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统地总结了科学实验的方法和经验
贝尔纳(1813~1878)发表《实验医学导论》,论证了在医学中采用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统地总结了科学实验的方法和经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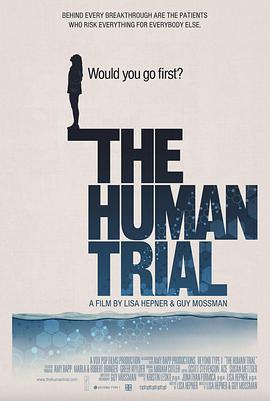 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医学把科学实验作为自己前进的主要车轮 但那时医学中科学实验主要在动物、微生物、人的离体组织和分泌物、包括人的尸体上进行,也就是说局限在基础医学的实验室中,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把基础医学称为实验医学以区别于应用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 临床医学中的研究对象是人,人体既不能伤害,人权也不容侵犯 在一般科学实验中,实验对象的命运取决于实验的目的和方法的需要;而在临床医学中,则恰恰相反,实验的目的和方法必须符合实验对象──人的需要和利益,而不能像对无机物或其他生物那样进行实验 所以长时期来在临床医学中,主要靠盲目的摸索来积累经验,治疗学几乎是建立在纯粹的猜想的基础上,任何一个人的“理论”都有机会被奉为教条,被几代人所遵行 临床医学研究方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对疾病的认识与治疗正确与否,难以检验,使得一些错误的认识与疗法流传几百年,而得不到纠正 动物试验可以给临床医学以很大的帮助,但由于动物与人有很大差异,动物实验不能代替人体实验,例如青霉素这一对人体十分有用而又安全的重要药物,对于常用的医学实验动物──豚鼠却是剧毒药 即使一种药物或检查治疗方法通过了药理研究及动物实验,第一次用于人体时总还有一定的风险 因此,医学的发展允许进行一定的人体实验,以取得经验 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靠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医生,用战俘和难民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这引起了社会对人体实验伦理法规的重视,后来确定了著名的受试者“知情同意”原则 这里“知情”指受试者对实验目的与危险能够理解的知情,“同意”则应是自由意志下的同意 现代的医学伦理学承认人体实验是医学发展所需要的,但为了防止人体实验的滥用,有许多严格的限制,如规定药物只能在完成药理、毒理等动物实验,证实其疗效和安全剂量后才能进行人体实验(称为临床前试验),再经过医学伦理学委员会的审查同意才能在人体试用 因为在医生严密的监护下,由少数人承担可能出现的风险,借此取得可靠的经验,比盲目地在广大人群中推广,使更多的人受害,更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医学伦理学要求在人体试验中应当使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得到最大的保障,因此,首先应考虑临床前试验的资料是否完备;其次,临床试验的设计是否合理,特别是受试者的安全有无保障,是否真正做到了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由于人体实验的特殊性,1960年代一些临床药理学家首先在药物疗效的临床验证方面,总结出伦理学可以接受的人体实验方法──临床药理学中的药效动力学方法;70年代一些临床学家又将科学的人体实验的方法全面地应用到临床研究的各方面,建立了临床流行学 检验新药临床疗效的人体实验称为临床验证,中国药品管理法规定:新药的临床试验分三期:一期临床试验是验证新药在人体内的可接受性及在人体内的药物代谢动力学,一般在健康人中进行;二期临床试验是疗效的验证,是新药验证的最重要的阶段,需要选择病人并设立对照组(给予安慰剂);三期临床试验是通过前两期后,新药在临床推广应用后的监测,目的是及时发现较少见或潜伏期较长的毒副作用 凡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人体实验,应视为非法 受试者从正常成年人及适宜的病人中选择,均以自愿为原则,男女数量最好相等,例数应视验证的需要而定,妊娠妇女和儿童(除非儿科方面的特殊需要)不作为受试者 并应强调:必须自始至终对受试者的安全负责,必须准备好应付意外的急救措施,对用药后的不良反应要给予有效的治疗 应给予受试者必要的报酬 中医中药的临床验证基本上也适用以上原则 根据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8月29日公布的初步报告,为了测试青霉素能否治愈和预防性病,美国研究人员竟然在1946年至1948年故意让1300多名危地马拉囚犯、精神病患者和性工作者染上淋病、梅毒和软性下疳等性病,其中只有大约700人得到某种治疗 截至1953年底,共有83名实验对象死亡 60多年后发现尘封档案这一令人发指的丑闻最初曝光于2010年秋天 在阅读已故医生约翰·卡特勒留下的档案文件时,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从事女性和医学史研究的专家苏珊·里维尔比惊讶地发现,卡特勒曾于上世纪40年代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秘密进行人体实验 里维尔比说,在得知这一惊天秘闻后,自己“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怎么也无法相信会有这种事 在一篇长达29页的文章中,里维尔比披露说,美国实验人员有时让囚犯、妓女或精神病患者喝下含有性病病毒的蒸馏水;有时为了让一些妇女感染性病,拿带有病毒的注射器划破她们的口、脸和手臂……而这些“人类小白鼠”对实验目的毫不知情 这些实验对象有的接受了青霉素治疗,有的则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 医学史上可耻的一页事情被曝光后,危地马拉政府立即予以强烈谴责 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称之为“违反人性的罪行” 危政府表示,“保留将这一事件提交国际法庭的权利” 危地马拉副总统埃斯帕达29日称,危地马拉方面已经找到5名非法实验的幸存者,并准备把他们送到危地马拉最大的医院进行检查,以确定实验对他们本人和家人所造成的影响 据介绍,这5名幸存者年龄在85岁左右 埃斯帕达表示,危地马拉政府将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然后决定如何应对 检查结果将于2011年10月由科洛姆提名组成的总统调查委员会公布 2010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被迫就此事向科洛姆表示道歉,强调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并下令组成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对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也联合发表了道歉声明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表示,这项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项目,“没有将危地马拉人当人来看待” 虽然对梅毒、淋病等性病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科研目标,但研究人员没有任何理由在明知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实验 该委员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特曼谴责“这是医学史上可耻的一页” 她说:“参与实验的研究人员连对人权最低限度的尊重都没有,实验毫无道德可言 ”据报道,这个委员会将在2011年12月发布最终调查报告,“评估该事件涉及的道德问题”,以“确保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受害者一直被蒙在鼓里2010年10月,曾有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类似实验不止在国外进行,在美国国内也发生过“10多次” 美国媒体2011年2月爆料说,上世纪40至60年代,美国政府曾打着“研究治疗方法和研发新型药物”的旗号,对国内的囚犯和疾病患者进行了“高达40多次”人体实验,包括让精神病患者感染肝炎病毒、让囚犯感染流感病毒以及向慢性病患者注射癌细胞等 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些实验仅仅出于研究人员的好奇,根本没有任何成果可言 事实上,在美国开展人体实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媒体早在1972年就曾披露,从1932年开始,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亚拉巴马州征召了大约600名黑人,秘密开展梅毒对人体危害的研究 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这些被无辜剥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 2022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一座监狱数千名囚犯曾被作为医学实验对象,实验内容包括向囚犯体内注射杀虫剂和除草剂 刘长秋(上海法学会生命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人体实验是现代医学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必经环节,正如世界医学大会在《赫尔辛基宣言》中所指出的:“医学进步取决于对人体对象进行实验的研究”(第四条)、“即使是最经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也必须不断地由科学研究来检验它们的有效性、效率、易利用性和质量”(第六条) 然而,人体实验也经常为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乃至机构和国家所滥用,以致酿成人类医学发展史上的悲剧性事件 美国在危地马拉所进行的性病实验就在此列 该事件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一次严重亵渎,其曝光对于向来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次嘲弄,充分暴露了美国人权外交的虚伪性,使美国对内对外所奉行的双重人权标准再次暴露无遗 同时,该事件的曝光也凸显了强化国际生命伦理法律规范的必要性,尤其是在直接涉及人类生命尊严的国际人体实验立法方面 医学的进步离不开人体实验,但很显然,人体实验的进行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律与伦理准则基础之上,否则,就很容易背离医学发展的公益性,沦为个别人乃至国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
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医学把科学实验作为自己前进的主要车轮 但那时医学中科学实验主要在动物、微生物、人的离体组织和分泌物、包括人的尸体上进行,也就是说局限在基础医学的实验室中,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把基础医学称为实验医学以区别于应用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 临床医学中的研究对象是人,人体既不能伤害,人权也不容侵犯 在一般科学实验中,实验对象的命运取决于实验的目的和方法的需要;而在临床医学中,则恰恰相反,实验的目的和方法必须符合实验对象──人的需要和利益,而不能像对无机物或其他生物那样进行实验 所以长时期来在临床医学中,主要靠盲目的摸索来积累经验,治疗学几乎是建立在纯粹的猜想的基础上,任何一个人的“理论”都有机会被奉为教条,被几代人所遵行 临床医学研究方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对疾病的认识与治疗正确与否,难以检验,使得一些错误的认识与疗法流传几百年,而得不到纠正 动物试验可以给临床医学以很大的帮助,但由于动物与人有很大差异,动物实验不能代替人体实验,例如青霉素这一对人体十分有用而又安全的重要药物,对于常用的医学实验动物──豚鼠却是剧毒药 即使一种药物或检查治疗方法通过了药理研究及动物实验,第一次用于人体时总还有一定的风险 因此,医学的发展允许进行一定的人体实验,以取得经验 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靠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医生,用战俘和难民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这引起了社会对人体实验伦理法规的重视,后来确定了著名的受试者“知情同意”原则 这里“知情”指受试者对实验目的与危险能够理解的知情,“同意”则应是自由意志下的同意 现代的医学伦理学承认人体实验是医学发展所需要的,但为了防止人体实验的滥用,有许多严格的限制,如规定药物只能在完成药理、毒理等动物实验,证实其疗效和安全剂量后才能进行人体实验(称为临床前试验),再经过医学伦理学委员会的审查同意才能在人体试用 因为在医生严密的监护下,由少数人承担可能出现的风险,借此取得可靠的经验,比盲目地在广大人群中推广,使更多的人受害,更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医学伦理学要求在人体试验中应当使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得到最大的保障,因此,首先应考虑临床前试验的资料是否完备;其次,临床试验的设计是否合理,特别是受试者的安全有无保障,是否真正做到了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由于人体实验的特殊性,1960年代一些临床药理学家首先在药物疗效的临床验证方面,总结出伦理学可以接受的人体实验方法──临床药理学中的药效动力学方法;70年代一些临床学家又将科学的人体实验的方法全面地应用到临床研究的各方面,建立了临床流行学 检验新药临床疗效的人体实验称为临床验证,中国药品管理法规定:新药的临床试验分三期:一期临床试验是验证新药在人体内的可接受性及在人体内的药物代谢动力学,一般在健康人中进行;二期临床试验是疗效的验证,是新药验证的最重要的阶段,需要选择病人并设立对照组(给予安慰剂);三期临床试验是通过前两期后,新药在临床推广应用后的监测,目的是及时发现较少见或潜伏期较长的毒副作用 凡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人体实验,应视为非法 受试者从正常成年人及适宜的病人中选择,均以自愿为原则,男女数量最好相等,例数应视验证的需要而定,妊娠妇女和儿童(除非儿科方面的特殊需要)不作为受试者 并应强调:必须自始至终对受试者的安全负责,必须准备好应付意外的急救措施,对用药后的不良反应要给予有效的治疗 应给予受试者必要的报酬 中医中药的临床验证基本上也适用以上原则 根据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8月29日公布的初步报告,为了测试青霉素能否治愈和预防性病,美国研究人员竟然在1946年至1948年故意让1300多名危地马拉囚犯、精神病患者和性工作者染上淋病、梅毒和软性下疳等性病,其中只有大约700人得到某种治疗 截至1953年底,共有83名实验对象死亡 60多年后发现尘封档案这一令人发指的丑闻最初曝光于2010年秋天 在阅读已故医生约翰·卡特勒留下的档案文件时,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从事女性和医学史研究的专家苏珊·里维尔比惊讶地发现,卡特勒曾于上世纪40年代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秘密进行人体实验 里维尔比说,在得知这一惊天秘闻后,自己“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怎么也无法相信会有这种事 在一篇长达29页的文章中,里维尔比披露说,美国实验人员有时让囚犯、妓女或精神病患者喝下含有性病病毒的蒸馏水;有时为了让一些妇女感染性病,拿带有病毒的注射器划破她们的口、脸和手臂……而这些“人类小白鼠”对实验目的毫不知情 这些实验对象有的接受了青霉素治疗,有的则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 医学史上可耻的一页事情被曝光后,危地马拉政府立即予以强烈谴责 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称之为“违反人性的罪行” 危政府表示,“保留将这一事件提交国际法庭的权利” 危地马拉副总统埃斯帕达29日称,危地马拉方面已经找到5名非法实验的幸存者,并准备把他们送到危地马拉最大的医院进行检查,以确定实验对他们本人和家人所造成的影响 据介绍,这5名幸存者年龄在85岁左右 埃斯帕达表示,危地马拉政府将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然后决定如何应对 检查结果将于2011年10月由科洛姆提名组成的总统调查委员会公布 2010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被迫就此事向科洛姆表示道歉,强调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并下令组成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对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也联合发表了道歉声明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表示,这项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项目,“没有将危地马拉人当人来看待” 虽然对梅毒、淋病等性病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科研目标,但研究人员没有任何理由在明知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实验 该委员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特曼谴责“这是医学史上可耻的一页” 她说:“参与实验的研究人员连对人权最低限度的尊重都没有,实验毫无道德可言 ”据报道,这个委员会将在2011年12月发布最终调查报告,“评估该事件涉及的道德问题”,以“确保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受害者一直被蒙在鼓里2010年10月,曾有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类似实验不止在国外进行,在美国国内也发生过“10多次” 美国媒体2011年2月爆料说,上世纪40至60年代,美国政府曾打着“研究治疗方法和研发新型药物”的旗号,对国内的囚犯和疾病患者进行了“高达40多次”人体实验,包括让精神病患者感染肝炎病毒、让囚犯感染流感病毒以及向慢性病患者注射癌细胞等 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些实验仅仅出于研究人员的好奇,根本没有任何成果可言 事实上,在美国开展人体实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媒体早在1972年就曾披露,从1932年开始,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亚拉巴马州征召了大约600名黑人,秘密开展梅毒对人体危害的研究 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这些被无辜剥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 2022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一座监狱数千名囚犯曾被作为医学实验对象,实验内容包括向囚犯体内注射杀虫剂和除草剂 刘长秋(上海法学会生命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人体实验是现代医学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必经环节,正如世界医学大会在《赫尔辛基宣言》中所指出的:“医学进步取决于对人体对象进行实验的研究”(第四条)、“即使是最经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也必须不断地由科学研究来检验它们的有效性、效率、易利用性和质量”(第六条) 然而,人体实验也经常为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乃至机构和国家所滥用,以致酿成人类医学发展史上的悲剧性事件 美国在危地马拉所进行的性病实验就在此列 该事件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一次严重亵渎,其曝光对于向来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次嘲弄,充分暴露了美国人权外交的虚伪性,使美国对内对外所奉行的双重人权标准再次暴露无遗 同时,该事件的曝光也凸显了强化国际生命伦理法律规范的必要性,尤其是在直接涉及人类生命尊严的国际人体实验立法方面 医学的进步离不开人体实验,但很显然,人体实验的进行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律与伦理准则基础之上,否则,就很容易背离医学发展的公益性,沦为个别人乃至国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